


9月到了,正是开学的季节,小朋友和大朋友们都要告别假期,重新回到学校,开始新的学习生活。今天,带来三篇文章送给即将上学的小伙伴,也送给那些再也不用上学的小伙伴,毕竟这是你们回不去的旧时光。

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(节选)
◎by.鲁迅
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,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。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,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,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下来罢,……都无从知道。总而言之: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。Ade,我的蟋蟀们!Ade,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!
出门向东,不上半里,走过一道石桥,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。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,第三间是书房。中间挂着一块扁道:三味书屋;扁下面是一幅画,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。没有孔子牌位,我们便对着那扁和鹿行礼。第一次算是拜孔子,第二次算是拜先生。
第二次行礼时,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。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,须发都花白了,还戴着大眼镜。我对他很恭敬,因为我早听到,他是本城中极方正,质朴,博学的人。
不知从那里听来的,东方朔也很渊博,他认识一种虫,名曰“怪哉”,冤气所化,用酒一浇,就消释了。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,但阿长是不知道的,因为她毕竟不渊博。现在得到机会了,可以问先生。
“先生,‘怪哉’这虫,是怎么一回事?……”我上了生书,将要退下来的时候,赶忙问。
“不知道!”他似乎很不高兴,脸上还有怒色了。
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,只要读书,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,决不至于不知道,所谓不知道者,乃是不愿意说。年纪比我大的人,往往如此,我遇见过好几回了。
我就只读书,正午习字,晚上对课。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,后来却好起来了,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,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,从三言到五言,终于到七言。
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,虽然小,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,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。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,静悄悄地没有声音。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,太久,可就不行了,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:——
“人都到那里去了?”
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;一同回去,也不行的。他有一条戒尺,但是不常用,也有罚跪的规矩,但也不常用,普通总不过瞪几眼,大声道:——
“读书!”
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,真是人声鼎沸。有念“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”的,有念“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”的,有念“上九潜龙勿用”的,有念“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”的……先生自己也念书。后来,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,静下去了,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:——
“铁如意,指挥倜傥,一座皆惊呢~~;金叵罗,颠倒淋漓噫,千杯未醉嗬~~……”
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,因为读到这里,他总是微笑起来,而且将头仰起,摇着,向后面拗过去,拗过去。
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,于我们是很相宜的。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。我是画画儿,用一种叫作“荆川纸”的,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,象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。读的书多起来,画的画也多起来;书没有读成,画的成绩却不少了,最成片断的是《荡寇志》和《西游记》的绣像,都有一大本。后来,因为要钱用,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。他的父亲是开锡箔店的;听说现在自己已经做了店主,而且快要升到绅士的地位了。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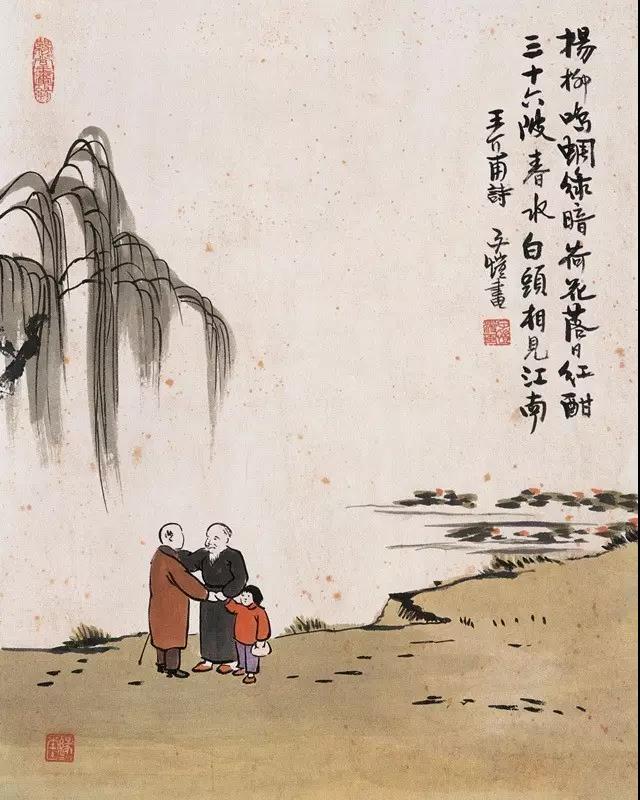
《上学记》(节选)
◎by.何兆武
我在北京上师大附中的时候,每一年开学教务主任都有一篇成绩报告,说我们今年暑假毕业了多少人,有多少人考上了北京大学,多少人考上了清华大学,多少人考上了南洋交大——就是上海交大。虽然我们是师大附中的,但他连多少人考上师大都不报,大概当时人们心目中就认为这三个学校是最好的,所以我脑子里边也总以为,将来我要上大学就应该上这三个学校。
1939年秋天我到昆明西南联大报到,一来就感觉到昆明的天气美极了,真是碧空如洗,连北京都很少看见那么好的蓝天。在贵州,整天下雨没个完,几乎看不到晴天,云南虽然也下雨,可是雨过天晴,太阳出来非常漂亮,带着心情也美好极了。而且云南不像贵州穷山恶水、除了山就是山,云南有大片一望无际的平原,看着就让人开朗。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:环境不同了。联大三个学校以前都是北方的,北京、天津不属于国民党直接控制的地区,本来就有自由散漫的传统,到了云南又有地方势力的保护,保持了原有的作风,个人行为绝对自由。没有点名,没有排队唱歌,也不用呼口号,早起晚睡没人管,不上课没人管,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。自由有一个好处,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,比如自己喜欢看的书才看,喜欢听的课才听,不喜欢的就不看、不听。这种作风非常符合我的胃口。
院士邹承鲁是西南联大的学生,对生物化学非常有贡献,上世纪六十年代轰动一时的胰岛素就是他们搞成功的。我看过一篇记者的访谈,记者问:“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,西南联大也不大,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?”他的回答非常简单,就是两个字:自由。我深有同感。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,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,看什么、听什么、怎么想,都没有人干涉,更没有思想教育。我们那时候什么样立场的同学都有,不过私人之间是很随便的,没有太大的思想上或者政治上的隔膜。宿舍里各个系的各级同学都有,晚上没事,大家也是海阔天空地胡扯一阵,有骂蒋介石的,也有三青团拥护蒋介石的,而且可以辩论,有时候也很激烈,可是辩论完了,大家关系依然很好。
学生的素质当然也重要,联大学生水平的确不错,但更重要的还是学术的气氛。“江山代有人才出”,人才永远都有,每个时代、每个国家不会差太多,问题是给不给他以自由发展的条件。我以为,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。没有求知的自由,没有思想的自由,没有个性的发展,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,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。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、背经,开口都说一样的话,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。当然,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,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,那会侵犯到别人,但是在这个范围之内,个人的自由越大越好。
我和母校西南联大的关系非常密切,我的两个姐姐是这个学校的,我的妹妹是这个学校的,我的姐夫、妹夫是这个学校的,我老伴也是这个学校的,所以这个学校跟我的关系算是非常密切。两个姐姐一个念化学,一个念经济,妹妹念中文,后来在人民大学自杀了,现在只有一个姐姐在美国(按:何先生的大姐于2005年3月在美国去世)。我自己从1939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(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),这正是一个人成熟的时期。
我在西南联大读过四个系——不过都没念好,高中统考填志愿的时候我问一个同学:“你考什么专业?”他说:“像我们这样不成材的只好读文科,像你们念得好的都应该读理工科。”因为那时候都觉得,没出息的才去念文科,这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,所以我一年级念的是工科,入土木系。说来也挺有意思,中学的时候我根本没想到将来要学什么专业,只是看了丰子恺的《西洋建筑讲话》,从希腊罗马的神殿,一直讲到中世纪的教堂建筑,我觉着挺有意思,于是就想学建筑。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,学的都是机械系的公共必修课,比如初等微积分、普通物理,这两门是最重要的,还有投影几何、制图课。第一学期我还认真地学,可是到了第二学期,兴趣全不在这些,于是决定改行,开始有意识地补充了一些文科知识。
那时候转系很方便,只要学分念够了可以随便转,我想搞文科,但不知为什么就选择了历史系,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了,也许有两个潜在的原因吧。第一我小时候在北京,看了好些个皇宫、园囿,从香山一直到北大、清华这一带,都是皇家园林,这就容易使人“发思古之幽情”。第二,那时候正值国难,小学是“九·一八”,中学是中日战争,刚一入大学就是二战,对人类命运也很关心,以为学历史能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。
不过我对繁琐的历史考据一直没有多大兴趣。有些实践的历史学家或者专业的历史学家,往往从一个小的地方入手考证一个小的东西,比如红学家考证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,把所有可能的材料都找出来,真是费尽心力,到现在还没有个结论。不过我觉得,即使有一天费很大的精力把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考证了出来,也并不等于理解了历史。而且,冯文潜先生教西方哲学史给了我很大的启发,让我感觉到,真正理解历史一定要提升到哲学的高度,不然只知道姓名、知道年代,你可以知道很多很多零碎的知识,但不一定就意味着你理解了历史。我想任何学问都是这样,最后总得有人做出理论的总结,否则只能停留在纯技术性的层面。当然纯技术性的工作也有价值,不过那不是我所希望的,我所希望的是通过学习历史得出一个全面的、高度性的认识。项羽说:“书能知姓名。”战争时期我们关心的是人类的命运,我以为可以从历史里找出答案,比如历史上有些国家本来很强盛,可是后来突然衰落了,像罗马帝国,中国的秦汉、隋唐,我希望探索历史深处的幽微,所以就念了历史系。
有些事情说起来很有意思。解放以后院系调整,冯友兰一直在北大呆了几十年,从组织关系上说,他是北大的人,死后应该把书捐给北大,可是他却捐给了清华。刘崇先生在台湾去世,他的书也是捐给清华,而没有捐给台湾大学,这也似乎不合常规。我猜想,大概他们觉得自己一生最美好、最满意的那一段时光,还是在清华,所以愿意把书捐给清华。我现在也八十多岁了,回想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候,还是联大那七年,四年本科、三年研究生。当然,那也是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一段时期,可是幸福不等于物质生活,尤其不等于钱多,那美好又在哪里呢?
我想,幸福的条件有两个,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、美好的,可是这又非常模糊,非常朦胧,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。另一方面,整个社会的前景,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,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,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。这两个条件在我上学的时候恰好同时都有,当时正是战争年代,但正因为打仗,所以好像直觉地、模糊地,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认为,战争一定会胜利,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,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。那时候不只我一个人,我相信绝大多数青年都有这种模糊的感觉。人总是靠着希望生活的,这两个希望是最根本的,所以那时候虽然物质生活非常之苦,可是觉得非常的幸福。

《上学记》节选
◎by.安宁
阿秀喊我去上学,我正光着脊梁骨在饭桌前吃饭,还眼泪汪汪的。那眼泪是刚刚被父亲罚背乘法口诀遗留的屈辱痕迹。我借机要逃走,父亲却在身后插了一刀:再不好好学习,等我去村东头找你们孔老师,让她在课上揍你!我吓得差点尿了裤子。可是在阿秀面前,又不好说什么,便飞快地扒拉完面条,嘴里嗯嗯啊啊地胡乱答应着,穿上背心,拎起母亲缝制的破旧书包,便跑出了家门,连阿秀是否被落在了家里,都不知道。
那孔老师好像千年妖怪一样,总也不死。她教完了父亲那一茬人,又教我这一茬。村子里好多人都是她的学生,她因此便有了某种打人的资格。而且打了学生,没有一个敢反抗的。就连家人,将孩子交给她的时候,都要特意叮嘱一句:不听话,您就好好打!她当然是真打的,而且一点都不含糊。她那桃木棍做的小教鞭,敲黑板震天响,她的嗓门,也比雷声大。而她打起我们的手心或者脸蛋屁股来,简直是监狱里在上刑。哪个家长要是敢说她打得不对,在村子里就别想做人了。大人们都说,小孩子不打不成器,孔老师打得好!
我知道盼结束上学的日子,是盼不到头的。这孔老师是个全知全能的人物,她能教一到五年级,批改一屋子的作业,有时候我们一年级和三年级的在一起上课,每个年级占一排桌椅,密密麻麻的,倒也挺热闹。
冬天的时候就更热闹了。孔老师规定,每两个人值日一天。于是这一天,我就会和阿秀从家里早早地起床,带玉蜀黍棒,赶到滴水成冰的教室里,哆哆嗦嗦地划着火柴,将烂树叶子、朽木棍子、玉蜀黍棒先点燃了,再慢慢地朝炉子里放炭。也不知我和阿秀到底是谁更笨一些,每次跟她合作,都得点个三四次,将教室里弄得乌烟瘴气的,才能将炉火给旺旺地撩拨起来。趁着同学和孔老师还没有来,阿秀瞅瞅四周,神奇地从兜里掏出一个地瓜来,而后放在炉子底下,用落下来的炭火碎末来烤地瓜。我问阿秀是不是前一天下井了?否则怎么掏挖出这么新鲜的地瓜来?阿秀得意:下井拿地瓜的活,都是我妹妹干,我只不过是让她帮我藏了一个,放在书包里罢了。我闻着那渐渐开始冒出香气的地瓜,有些后悔自己没从家里带花生或者粉皮来,烤着吃。我们两个人还围着炉火,边烤手边唠起嗑来,内容从烤地瓜到煮的地瓜干,再到豆扁子咸糊涂,还有家里腌的咸菜疙瘩,就连糊锅的时候锅底上的干疙疤也好好地描述了一番。最后两个人说的有些困了,便趴在桌子上睡过去了。
等我们醒来的时候,孔老师的教鞭已经恶狠狠地敲了过来。我忽然间想起地瓜来了,却并没有寻到那浓郁的香甜味,是等到快要下早自习的时候,才从阿秀传过来的纸条上得知,那可怜的地瓜,已经被孔老师给扔到冰天雪地里去了。我的心顿时跟那地瓜一样,冻成了一块冰疙瘩。
好在早自习并不太长,老和尚念经一样摇头晃脑地读完了课文,我们便排着队唱着歌回家去吃早饭。我在路上跟阿秀探讨,那个地瓜会不会被孔老师给拾回教室去,重新烤烤吃了呢?阿秀刚要说话,前面的领头羊大队长,便来吼我们:走齐了!唱响亮一点!我只好忍饥挨饿,高唱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。不过这样的“酷刑”,等一拐过冲着学校的大道,便再也没用了。我和阿秀率先冲出队伍,奔回家去。母亲早就在村口等着我了。她见过一副饿虎扑狼的模样,便训我:读书如果跟吃饭似的有能耐,你娘我将来也能跟你享福了!我心里想,等我像村子里三祥一样当了工人,一定让你天天吃好的喝辣的!不过人家三祥是“接班”的,子承父业,还因为当了工人地位高,领回来一个烫了爆炸头的漂亮媳妇。我呢,将来当了工人,会不会给爹娘领回一个穿喇叭裤的“二流子”来?不过那事想来太遥远了,什么时候能够摆脱孔老师的教鞭还不一定呢,母亲她想让我当工人,也想得忒远大前程了点。
早晨的烦恼,晚上转瞬便逝。下午五点去上晚自习的时候,我和阿秀都从家里带着煤油灯。我多长了个心眼,从家里大瓮里抓了一把黄豆放兜里藏着。等晚自习上到一片灯火通明,孔老师也有些被煤油灯给熏得鼻孔透不过气来,微醺着脑袋去了办公室喝水,我们便开始肆无忌惮起来。我取出早就洗干净的放清凉油的小瓶盖,那瓶盖上拧了一道铁丝。我将几粒黄豆放到瓶盖里,然后便老头钓鱼一样,悠闲自在地持着那铁丝,在煤油灯上晃来晃去地烤着。烤料豆的当然不只是我一个人,于是教室里便充溢了浓浓的豆子或者玉米的香味。阿秀凑过脑袋来,咽了几口唾液,问我:啥时候能熟呢?千万别再被孔老师给没收了。我白她一眼:不能说点吉利话吗你?阿秀吐舌头:没事,她要来了,不熟我也吞肚子里去!
那料豆当然最后还是烤熟了的。于是我们的自习,便上得有滋有味。吃完了料豆,自习也就结束了。阿秀早就将挖来的朽木,分给我一块。她还很贴心地在上面抹了一层蜡烛油。于是放学的路上,我们便寻到了另外一种乐趣。一路上那黑幽幽的麦田,也不再那么可怕。一群人举着火苗很旺的朽木,唱着歌回家去。歌当然不再是领唱的,都是自己胡乱哼的欢快小曲。大队长也不再施展他的威风,他家离得远,为了能在没有路灯的村子里一路畅行,他还得向我和阿秀讨好,求我们多分给他一点朽木疙瘩用。阿秀有时大方,我却永远都对他小气,不给,就是不给!反正下学期他就不当大队长了,我怕他做什么呢?!
再长一岁,我们就不再这么幼稚地排队唱歌回家了。不过歌还是要唱的,只不过是在小小的校园里,由孔老师的儿子来教。孔老师的儿子是在部队当兵回来的,人长得年轻帅气,而且不像孔老师那样,天天被人欠了钱一样板着脸,所以他立刻风靡了整个校园。就连看大门的大爷大娘夫妻俩,也被吸引来,看我们在花坛前声情并茂地唱歌。他唱歌那么好听,以致于一首斗志昂扬的革命歌曲,在我们听来,跟浪漫情歌一样悦耳动听。小女生们都被这个大哥哥给迷倒了,教我们唱完了歌,还不肯放他离开,都哗啦啦地围过去,哥哥长哥哥短地叫个不停。我人好面子,就远远站着,看他眉飞色舞地当着老师。我有些嫉妒,尤其看一向羞涩的阿秀,竟然也泥鳅一样挤进了人群,更加地不悦。班里的文娱委员明明,站在最前面,一脸崇拜地望着军人哥哥,嘴唇微微张着,好像要亲上去了一样。我忽然间生了气,丢下被人群挤得东倒西歪的阿秀,冲进了教室。我要将送阿秀的铅笔刀拿走,而且再也不给她了。我想。
好在孔老师不平凡的儿子很忙,不会天天来教我们唱歌。所以我跟阿秀的友谊,也就微微挣了一下,又恢复如初。而且,更好的一条消息是,孔老师不再跟我们一直教到五年级了。新换的班主任老师,虽然也姓孔,却心宽体胖,每天乐呵呵的。我于是一下子有转世投胎、重新做人的感觉。那时我的作文开始稍见成色,于是忽然间从备受冷落者,华丽转身,成了班主任眼里的香饽饽。
为了区别两个孔老师,我和阿秀私下里叫低年级的为老孔,我们高年级的,当然就是小孔了。小孔老师其实也已经三十岁了,而且,她的儿子孔磊磊没有考上初中,于是留了级,跟我们做了同班同学,兼我的同桌。小孔对我偏爱,自然将自己的爱子安插在我的身边,一为互相帮助,二为我能帮她监督这个贪玩的儿子。不过,做老师的眼线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美好。比如因为走得太近,假如忽然间发现了小孔老师的瑕疵,到底该不该跟她的儿子孔磊磊说呢?
事情发生得有些突然,让我没有做好准备。午休的时候,班里的学生都将带来的麻袋铺在教室的红砖地上睡觉。很快周围就起了一片香甜的鼾声,我觉轻,听着那些鼾声,怎么也无法入睡。于是便偷偷地透过指缝观察身边的动静。我先观察到的,就是用课桌拼接起来的“床”上,胖胖的小孔老师的屁股。那屁股因为离得近,就被放大镜放大了一般,看上去愈发地丰满硕大。我闲得无聊,正研究着小孔老师红裤子里面会有什么颜色的三角内裤,校长忽然就走了进来。我知道校长是来检查午休的,就赶紧假装睡着了,将手蒙得更严了一些。但还是克制不住好奇心,我跟着校长的黑布鞋,观察他双脚的运动轨迹。很快,那脚在教室里走了一圈后,停在了小孔老师的身后。
我顺着校长的双脚,一点点朝上看去。就在我将眼睛落在小孔老师屁股上的时候,我们天天一脸威严的校长,竟然,用右手亲昵地摸了一下小孔老师又圆又大的屁股!我被校长的这一举动,给吓坏了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,除了将眼睛紧紧地闭上,假装什么也没有看见。可是,我明明都看见了,而且,我还听见小孔老师含嗔带羞地叫骂了一下。小孔老师跟校长打情骂俏,那么他们之间肯定发生过什么!我迅速地在脑子里这样总结判定。
校长很快就离开了教室,可是我的心里,却被这个天大的秘密给憋的,快要疯掉了。但我却谁也不能够告诉,连阿秀也不行,因为我怕她会快嘴快舌地转给孔磊磊,并引发一场学校大战。我就这样每天坐在孔磊磊的身边,看着他的妈妈小孔老师,在讲台上眉飞色舞地讲课,因为胖,全身的肉都跟着眉眼晃动。我心里的那个秘密,也这样不安地晃来晃去。我还害怕见到穿黑布鞋的校长,听到他在校园里,跟几个老师谈论找学生收割麦子的事情,我就怕,好像他要将知晓秘密的我,用镰刀给收割掉一样。似乎一下子,我在这个小小的校园里,就有了校长、小孔老师和孔磊磊三个强大的敌人,他们虎视眈眈地窥视着我,监控着我,让我焦虑,也让我心惊。
可是那个秘密,却好像长了翅膀,自己从我心里飞出去了。我常常看见几个老师在小孔老师走过后,站在一起窃窃私语,还很诡异地笑着。而校长也脾气有些怪异起来,升旗仪式上,总是在国旗下将我们大骂一顿。小孔老师呢,也在某一天,忽然间脾气暴躁,一上课,就气汹汹地检查我们的背诵,而后在孔磊磊背不出一首古诗的时候,啪一下将黑板擦摔在了地上,并飞快地朝我走过来。我吓坏了,不知道怎么办好,身体完全无法挪动,好像被钉子钉在了地上。我想小孔老师会不会杀了我?如果她一巴掌打过来,我是逃走还是立在原地?如果她联合校长将我开除了呢?就在我胡思乱想的空当,孔磊磊忽然间站了起来,并朝教室的后面跑了过去。而小孔老师则顺手操起我和孔磊磊一起坐的长板凳,追了过去。我的屁股,被无意中抽离了板凳,只觉一空,扑通坐在了地上。当然没人看我的笑话,大家都大气不敢出一口,紧张地注视着小孔老师在教室里追着孔磊磊跑啊跑,跑得两个人都气喘吁吁,却找不到什么理由停下这场悲情表演。最后,是小孔老师跑不动了,一屁股坐在了讲台上。而孔磊磊呢,则趁机溜出了教室,跑出了校门,右拐躲进一墙之隔的大队办公室去了,那里有他天天用大喇叭广播村里重要消息的爷爷。
小孔老师也就在这时候,开始哭了起来。她哭得伤心极了,好像我们都能够懂得她的悲伤一样。我想她一定不是因为孔磊磊背不上来古诗才这样气急败坏的,她其实跟我一样,被那个校长摸了屁股的绯闻,给折磨得心力交瘁。可她又和我一样,谁也不能说。她就那样一只手捂着半边脸哭啊哭,哭得眼睛都红肿了,一节课也快要上完了,这才慢慢止住了。
我们都以为小孔老师什么也不说,就夹着课本走出去了。但她却将头一昂,又恢复了昔日的气势,用教鞭指着我们骂道:你们一个一个跟孔磊磊一样不是什么好东西!我用板凳砸他,你们竟然没一个站出来拦着,都瞎眼了啊,你们以为我愿意砸他啊,我砸我儿子我心里难受得很!你们这群忘恩负义的家伙,等小学毕了业,肯定都是白眼狼,一出门就将我给骂死……
小孔老师就这样说啊说,跟片刻前的哭啊哭一样无休无止。以致于下节课的数学老师已经站在了门外,有些不耐烦地抽着烟等着,就差踹门进来了,她还不肯停止叫骂。是上课铃声烦躁地催了第二遍,她才朝我们丢下一个白眼,气呼呼地走出了教室。
我一直怀疑,那个秘密是被我无意中在午休的时候,睡梦里说出去的,又恰好被谁给听去了,然后才瘟疫一样传遍了整个校园,包括村子。我也因此惶恐不安,怕小孔老师射过来的每一个意味深长的视线。直到有一天,我们拍了毕业照,大家纷纷作鸟兽散,所有的惧怕,也跟着打包带回家去的书本文具,一起离开了校园。
而小孔老师,作为民办教师,和老孔老师一样,也跟着我们,一起离开了喜怒哀乐许多年的校园,重新成为村子里,耕作土地的农民。